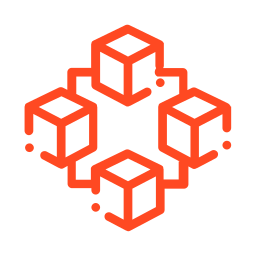散文 | 母亲的酸菜
黄耀红
酸菜,自乡野来,难登大雅之堂。看起来黑不溜秋,闻起来则一股浓郁的酸味。通常它被切成短短的,晒得干干的,以旧报纸包着,或被塑料袋拎着,或塞在车子后备厢,满身都散发出寒素与卑微的气息。
然而,做酸菜是母亲一辈子的习惯。
对她来说,萝卜、白菜、排菜、蕹菜,都可以做成酸菜。当然,最经典的还是排菜酸菜。
排菜似乎专为酸菜而生。它的叶子不像红菜、白菜那样规整,参差郁郁,形如齿状,较蕨叶则远为疏朗。排菜从地里砍回,会有一股刺鼻的青色气息。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吧,排菜从来不会像其他小菜那样即炒即食。一般情况下,人们会将其以沸水烫煮,再放到盆子里隔一两晚,待它稍稍变黄后炒食,既无异味,又极爽口。人们赋予这道菜一个极诗意的名字,叫雪里蕻。
这只是最简单的排菜酸菜,更普遍的还是晒干后变黑的那种。
小时候,家里缺吃少穿。然而,再怎么清贫,一碗酸菜还是有的。那年月,乡下连豆腐皆为稀物,记忆里的酸菜汤就那么黑黑一碗,汤里浮着切碎的黄红辣椒。将酸菜汤泡到饭里,很有点酱油的味道。
酸菜除了开汤之外,炒辣椒亦是绝妙的做法。每年辣椒开园的日子,将青椒佐以酸菜爆炒。出锅之后,青与黑点染于白瓷碗里,油滴滴的,软软的,并不辣,恍如一碗春色。
酸菜也可用于蒸肉。相对于豆腐来说,那是难得的奢侈。到了过年,团年饭上往往会有一道保留菜,叫酸菜蒸肘子。肘子,即从猪的后腿处剜下的一团肉,半肥半瘦,圆鼓鼓的,肉皮则往往被熏得黑里透黄。待其蒸熟之后,在腾腾热气里,肘子泛着微光。而碗底那黑黑的酸菜,也在油亮中兀自柔软爽滑,成为南方过年的乡味。
记忆里,每当低矮厨房里弥漫起酸菜蒸肘子的异香时,年关就已到了。那时候,酸菜的味道里交织着一家人劳作后的天伦与幸福。
对母亲来说,酸菜则是她的日常,是她的生活,亦是她与世界相往来的方式。几十年来,酸菜与鸡蛋、红薯、萝卜、冬瓜一起,成为母亲在乡间的礼尚往来,成为她捎给城里亲戚的心意。
吃过母亲做的酸菜的人,都说极好。有一天,我和她坐在冬阳里聊天。母亲对我说起酸菜的做法,既感意外,又觉开心。她说,当排菜长到一定时候,你把它从地里砍回来,以清水洗净,太阳下稍稍晒一晒。待排菜梗变软了之后,收回来,匀匀地切碎,堆成一堆,再以手反复揉搓,最后装入坛里。注意坛沿里一定要加些水,以确保坛的密封。这样过了一两天,待菜变酸之后,又全部将它们从坛里掏出来,摆到篮盘或筛子里再来晒。大概晒了一两天太阳,干了,再以柴火去蒸。
“那蒸多久呢?”我问。
“根把香久”母亲说。突然觉得母亲表述时间的方式如此特别,她向来不说多少分钟,而说“根把香久”“碗把茶久”“餐把饭久”。她的时间,就是她的生活。
酸菜在灶上蒸过之后,复在阳光里晒,直晒得它们全部黑黑的,焦干的,再以袋密封。
在凛寒冬日,特别是雨雪霏霏的黄昏,当酸菜摆上餐桌的时候,不知还有多少人会想起它的前世?那原是菜园一畦一畦蓬勃的春光,也曾是花开叶绿、蜂飞蝶舞的时光。
有人不喜欢它的酸味,其实,那些青绿的生命正是以酸的方式开始了珍藏。也就是说,酸就是一切青青菜畦抵御时间的方式。
其实,酸菜的味道远非口舌之虞,它分明就是一种朴素里品味丰富的境界。因为,生活从来不只是五彩斑斓,它更可能是五味杂陈。
>>我要举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