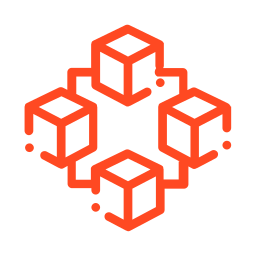散文 | 飞鸟滑过的天空
文 | 袁长江
我目之所极的天空,飞鸟滑过的一隅。
大多时候,我能看到的天空,就是抬头所能看到的一点,很小,也不太规则,街道上的房子零乱而各有特色,当然,这不是主因,七七八八的电线光纤如同陈年的蛛网,所以,天空被划作了很多块,像调色板,朝霞,夕阳,蓝天白云或是乌云密布,四季分明,颜色纷呈。
晴天的早上,天是瓦蓝瓦蓝的,风很轻,也很有凉意,是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候,抬头看一眼初升的太阳,就能打一个很响亮的喷嚏,必定有人在旁边恨恨地说:本来就热——俚语里说“狗打喷嚏天大晴”,这是一个很隐晦又众人皆知的玩笑,没有人会生气,也不会恼火,因为他马上又会来一个——这个必定是带着所有人的笑声,连他自己也自嘲笑道:莫念莫念,俚语里,被人念叨惦记也是会打喷嚏的。
可以看到空中的星星或是月亮,月亮迟迟不肯落下去,有时候会要等到太阳升起来,颜色才渐渐消失。当然,也能看到月亮又大又圆的时候,尤其是秋夜,繁星点点,是云还是银河,我不得而知。月光朗朗地照在同样狭窄的街道上,我有时会到天台上去,想着是不是离月亮越近,更能看清它的样子,天台上的月光一样的亮堂,像茅山道士所画的月亮,触手可及,能照到我的心里,每一个角落里都充满光泽,自己也变得澄澈通透,我只能匆匆下楼,再呆下去,深恐自己就会消失融合在月光之中。
有月光,也有飞鸟,街道上越来越多麻雀、燕子,还有成群的野八哥,鸟叫声能充斥你的每一个时间节点,清晨,正午,子夜。你还没醒来,聒噪的麻雀能占据你的整个窗台,比闹钟还要准时,让你以为太阳早就晒屁股了,可一起来,天刚刚亮呢。子夜里鸣叫的鸟躲得很远,在街道外的树林里,夜深人静,正是我无法入睡的时候,我听得出是杜鹃,那叫声有点恐怖,东风远去,杜鹃仍没完没了地叫个不停,直到啼血方止?真正瘆人的是猫头鹰,毕竟,潜意识里会认为它的叫声带了某种不吉之兆,尤其是在你被生活各种不顺裹挟不眠的时候,那叫声会让你惊慌失措,总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,会一遍遍检索自己的言行举止,结果只能是又一次失眠。
最新奇的风景,在那一小片的天空里,晴天的黄昏总能看到,银光锃亮的飞机变得很小很小,拉着长长的尾迹,于是有人在喊:“快看,飞机放路线了!”很笔直的线路,一会儿就吹散了,只剩下淡淡的痕迹,像是一抹轻轻的云,不一会又有一架或更多架飞机拉出线路。有一次不是飞机,而是一个拉着长长喷焰的物体,在遥远的天幕上飞过,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,UFO?不是,究竟是什么,第二天新闻里可能有报道。
非常的神秘!
更多的时候,天空只有云层,夏天,云层堆积,白亮白亮的,似乎随时有坍塌的危险,没有了云,天便蓝了,要命的蓝色,云层薄如羽絮,高温持续,恼火的天气。
最乏味的是下雨,大雨或小雨,春雨或夏雨,完全不同的章法,但是一个样,下雨天必定就是无聊的天气,街上行人稀少,诊所里门可罗雀,尤其是连续的雨天,春天,能下到人心里长霉,跟抽屉里的中药材一样,你一不留神就长霉了,让人无所适从——霉药季节雨纷纷,乡村医生欲断魂。当然,闲有闲的好,没有病人造访,无聊且繁琐的公卫资料可以推到一边,大可以把脚翘到桌子上,翻出一部看过多次的老电影,打发一下时光。如果是晚雨,是要抿一口小酒,这个时候,大约是不会有人念叨苛责的。
可惜下雪天太少,不然可以看雪花迷乱了整个街道,街道很快变成白色又因车辙足迹变得零乱不堪;雪停了雪化了,对面楼顶上会滑下大片大片的积雪,看似重重地砸在街道上,没有人受伤。因为下雪的日子太少了,要堆积到那么厚的时候更少,可惜了,不然看到有人被积雪砸中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。放心,不是我鬼马,这个不会有人受伤,那雪太薄,太薄,比夏天女孩子的裙子还薄,很多时候都只是我的想象,让人疑心南方是不是从来不下雪。
于我而言,这种生活早已习惯,毕竟不是倒处跑,生活圈子便局限于小街一隅,街上人来人往,美女不少,阿猫阿狗也不少,生活乏味,但也得过下去。电影《肖申克的救赎》,我看过几遍的老电影,让人羡慕的,不是主人公逃出生天大仇得报的那一刻,而是他为狱友们赢得了一桶啤酒,在早春的天气里,一帮人似乎自由了,闲适地在楼顶喝酒——我以为,心灵的自由才是真的自由。
这是我的天空,生活只能给我这个状态,只能给我这个范围,所以不必抱怨什么,你说是与不是?天空虽小,毕竟有飞鸟滑过,何况还有风花雪月呢,当然,这几个字只能分开读,有花还有雪,可风是风,月是月,此中并没有风月。
>>我要举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