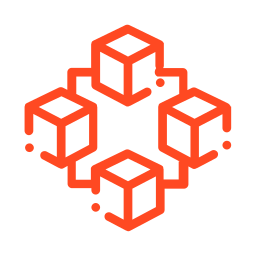散文 |关于树的个人记忆
文 | 戴俊英
晚报发了篇《彩色长沙 全城斑斓》,作者笔下的树既是个人的,也是关于一个城市的整体记忆。文字里有的感觉是相通的,比如春天四月雨后香樟树蓬勃而生的嫩绿的芽,芙蓉北路、人民西路的银杏树,一路读来,心潮澎湃,竟激起心中许多关于树的记忆。
树于在长沙乡下长大的我,是缤纷灿烂,还带着香甜味儿的。爷爷是农民,却是位有些不一样的农民,好读书,会织漂亮的竹篱笆,会编草绳、弹棉花,最重要的是会种果树、会嫁接。房前屋后,桃、李、梨、板栗、柿、橘、柚子,物质匮乏的上世纪70年代,这样一个园子,对一个孩童而言不啻一座宝库。从春天次第开放的花儿起,树的颜色就是白的、粉的、绚烂的,夏天的树是香的、甜的,点点橘子花、柚子花点缀在绿叶中,风拂过,清淡怡人。夏末,苹果李、脆白桃、叫不出品种的梨,一茬茬上桌。果实味道不好的果树,爷爷会重新嫁接,然后新的一年会有新的品种的桃、李。秋天的树,是最值得歌颂的,绿绿的板栗刺球儿,成熟的颜色会变暗,会裂开,露出黑皮包裹的板栗。青球坚实坚硬,用脚在地上擂开,会露出白色咖色相间的板栗。柿子树掉了叶子,果实渐渐变成红灯笼, 橘子也红了,红得与柿子不一样,偏黄。大门前柚子树冠已如华盖,枝繁叶茂,果实累累,远近闻名。一棵树,每年可以收200多个柚子,味道酸酸甜甜。
爷爷走后,叔伯辈们各自开枝散叶,分家而立。那些果树,大多凋零,柚子树也没了。前几天,回爸妈的院子,蓦然在房子东侧墙边发现一棵果实累累的高大柚子树,依稀相熟。问爸爸:这是爷爷种的?老爷子答:是的呀!记得爷爷生命的最后一段,在这个院子里住过,一茶一座,翻看金庸的《鹿鼎记》,编草绳。不知他何时种下了几棵柚子树。原来,生命也以这样一种方式在传承啊,那一刻,有些呆。
八九岁,我们随当兵的父亲进了城。部队大院里,一切整齐划一,玉兰树、香樟树,整整齐齐、高高大大,和大院里随处可见的绿军装颜色高度一致。只在楼下的三岔路口,有一棵硕大的银杏树,春天长新叶,夏日结果,秋日染金黄,而后叶落,绚烂后归于平静,来年再战。那棵银杏,足够大、足够高、足够美,承载了一个十几岁女孩种种光怪陆离的小心思。很多年后,一个刮风下雨的冬夜,开车经过五一大道,也遇到一棵这样的银杏树,足够高大、足够美。南方的湿冷的冬天也足够冷,旁边的树木已凋零,只有那棵银杏,顶着一树金黄,依然站立在风雨中,蓦然想起的是一首五月天的《倔强 》。我们都一样,年轻又彷徨。不怕千万人阻挡,只怕自己投降。少年的自己,中年的自己,都在眼前的这一棵树前和解,初闻不识曲中意,再听已是曲中人。
去年秋天,高三的女儿不肯去学校,在家里睡了整整一天,我不得其法,只能跟老师告了假,捧一本书,静静陪伴。晚上八点,问她:我们出去吃个饭可好?她问:可以吗?当然可以啊。我们穿上薄棉衣,去一家岭南餐厅吃了饭。女儿细声说,我晚上十点后想去教室把书搬回来。我说:好!
饭后时间尚早,我们俩开着车在城市转悠,穿过五一大道,走到芙蓉北路,倒回来,再到人民西路。这座城里的银杏,很有意思,城中各处的银杏大多已落叶,只有芙蓉北路(过五一大道到伍家岭路段)、人民西路一带的银杏,树形高、树冠大而圆、树叶浓密、颜色亦美。
车行缓慢,女儿悠悠而叹:真美,妈妈,我好久没出门了。后来,女儿去教室搬回了书,在家呆了一周,又回了学校。一年后,再次经过深秋的人民西路,女儿叹:那时候,怎么会那么伤心呢?今天接到一个同事打来的电话,诉说高三的侄女儿每逢考试会紧张、哭泣。我只能告知我们所经历过的过往,不知是否能帮到同事。
那篇文字里,有那么多的树,有熟的不熟的,乌桕、无患子、红枫、栾树、悬铃木、黄栌、水杉,有时会随着文字刻意寻去,也有不经意走过时不期而遇。如此让人心生喜悦,只因为一棵棵、一片片生长的树。
>>我要举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