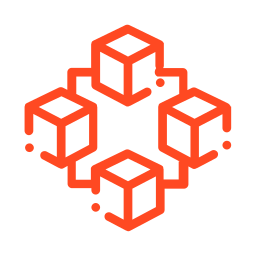散文 | 一根萝卜
文 | 熊其雨
冬吃萝卜夏吃姜,讲的是时令与节气的故事。在繁华都市沉浮,春节期间每每游走于觥筹交错之余,都应怀有一种“应时而食”和“不时不食”的养生哲学。既给身体难得的偷闲,也不失为一种大智若愚。
那是大雪如盖车马稀的岁末。冰凌倒挂,推开菜园柴门,随外婆拿铁锹和锄头入园,一铲铲敲开冻得梆硬的泥巴,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截乌青色的萝卜,揪掉萝卜叶,下方是粗如手臂的白萝卜。放井水拿干稻草搓净泥巴,洗净切拇指状粗条,搭配腌制腊鱼取下的新鲜鳙鱼头、鱼尾,掺些鱼肠、鱼白和鱼籽,吊锅里搁些菜籽油、姜丝、华容芥菜丝,爆香窊一瓢长江水焖煮,铁锅下是烧得正旺的构树蔸、白杨树蔸,好事者放的臭皮柑和苕块,冒着香气和热气。记忆里,那是一座有天井的老房子,房梁中央的毛玻璃被熏得发黄依然透着光,柴屑灰肆意飘舞,如快意潇洒的浪人。老人和小孩围坐一团你一筷我一勺,血气方刚的汉子拿一小盅子,嘬一口谷酒下喉,一烫带三鲜。虽是萝卜小菜却也自得其乐,其中的大道至简,试问几人懂?
湘北大山里,勤快的农家不搓麻将喜农事,用时光和一亩三分地较劲,为了迎接子女归巢,她用一双皱手创造了一钵钵舌尖上的滋味菜。红滴滴的樱桃萝卜搓盐,放在芦席上风吹日晒,待到脱水起皱拌剁辣椒进坛密封,吃时切滚刀块放土麻油,开胃消食。倘若席间还有脆甜香的揉萝卜菜和蓑衣萝卜,我想,萝卜界的“满汉全席”也足以让大肚便便者大快朵颐了。
荷包稍鼓,疲于农事的人们,大多迷上了喝早酒。记忆中的清早,街边小店的竹屉笼冒着热气,一钵嫩白的蒸萝卜丝勾人味蕾。父亲带着我“馋口水”,夹几片卤香干、一颗卤蛋,切些猪头皮肉等,三三两两的熟人就着白酒当街小酌,卤菜的香、白酒的辣、萝卜的甜、人性的真,通通倒进喉咙化作一天的“鸡血”,仿佛能够消解人生的酸甜苦辣和百味交集。
一碗蒸萝卜丝的甜,足以慰藉记忆之苦。如今,老家禾场上有一棵高20多米的树,树皮为黄褐色,树干空心却挺拔,光怪陆离地伸向天空。父亲共有七兄弟,因为家境贫寒,他和几个哥哥曾被过继到本家的远方亲戚家。那个年代,爷爷靠养鸭和挑鸭蛋到圩场卖,父亲也一度吃过这种不知名树的树皮和树根。常听人讲,大家吃的油是棉籽油,饭桌上最常见的就是萝卜白菜。没有荤腥不开胃,奶奶就变着法做菜,煮萝卜、酱萝卜、泡萝卜、辣椒萝卜丁……
父亲说,蒸萝卜丝时,需取霜打的本地白萝卜,用铁刨子或菜刀切薄片成细丝,抖散后均匀地撒上粘米粉,蒸锅内水开后,铺纱布放萝卜丝猛火蒸十来分钟,待表面无明显干粉,筷子搅动起膏粘筷时,放熟猪肉、剁辣椒和麻油拌匀,口齿留香。
转眼年已过,萝卜长势好,寻一蒸笼上灶台,岂不妙哉?
>>我要举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