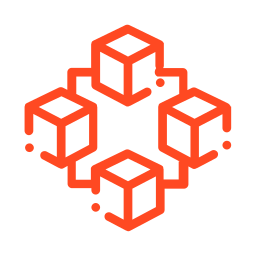散文 | “挑”野藠
文 | 刘新昌
看到野藠,让我莫名想起《还珠格格》里紫薇问乾隆的那句经典台词:“您还记得十八年前大明湖畔的夏雨荷么?”
野藠,似乎也是“薤爸爸”散落在乡下的一个黄毛小丫头,别看它长得瘦弱纤细,却焕发着勃勃生机和特立独行的香,那香,沾着泥土味,半是乡野,半是妩媚。它有一个亲姐姐——藠头,许是血脉相连的缘故,二者叶子的形状基本一致,都是三角形中空管状型,且里面凹进去形成一条长长的半圆形斜槽。
别看野藠和藠头长相相似,但生活习性却大相径庭。藠头,是人工驯化培育的新物种,而野藠,是自然进化的纯野生物种。藠头成簇生长,多个鳞茎挨挤在地下有限的空间里,抱团取暖,因拳脚施展不开,被挤成了长卵形;野藠呢,野惯了,它才不跟你挨挨挤挤,它一个鳞茎就独霸一个生活空间,它的宗旨是,活着就要无拘无束,它长着长着就成了圆球了。
可藠头毕竟是人工培育的,自身条件比野藠好得多,因此,不管是地上叶片还是地下鳞茎,都明显比野藠粗壮硕大得多。这好比一个是城里的大家闺秀,一个是乡下的山野村姑,大家闺秀家庭条件好,长得白嫩娇滴、富贵养眼,山野村姑呢,物质基础虽然差点,但顶不住它倔强要强、泼辣霸蛮,倒也一茬又一茬地生长着,生生不息。由于藠头和野藠的鳞茎同功同效,《中国药典》拿她们两姐妹没办法,都叫她们为“薤白”。
药典分不清的事,饕客们却如数家珍。藠头,因为鳞茎肥厚,洁白晶莹,自然是吃头。汪曾祺就曾在《葵·薤》一文里写道:“湖南等省人吃的藠头大多是腌制的,或入醋,味道酸甜;或加辣椒,则酸甜而极辣,皆极能开胃。”而野藠呢,鳞茎细小,叶子细长,以吃叶苗为主。嫩嫩的野藠叶挑回家,用清水冲洗干净,炖豆腐、炒鸡蛋、煮腊肉,皆是桌上美味。
只是,在我看来,吃野藠只吃叶苗的说法是一种懒人做法。其实,野藠头泡出来的酸菜,比人工培育的藠头好吃得多。我的老家湘中属丘陵地带,气候温润多雨,非常适合野藠生长,山坡上,水沟旁,菜地里,到处都有。每年农历十月过后,树木开始凋零,野藠却悄悄生长,到来年的暮春时节,野藠开出了细碎的花朵,此时,最宜去野地里挑野藠。老家人挑野藠,不用“挖”,不用“扯”,也不用“拔”,而是用“挑”,个中缘由,到现在我才慢慢玩味出来。挖、扯、拔,皆费力,还具有挑战性和风险性,黄庭坚就曾有诗云“意根难拔如薤本”,可见要将野藠头从土里拔出来,并非易事。而“挑”,就不一样了,轻轻松松,四两拨千斤,最能将寻找到野藠的娱乐性和愉悦性表达出来。
小时候,我最喜欢跟母亲去野地里挑野藠,每年春夏,绿意葱茏的野藠,一簇簇,一丛丛,躲在杂乱蓬松的草丛里,母亲用一根削尖的木棍,在野藠旁边轻轻一撬,圆滑白晳的野藠头,便连须带茎从泥土挑了出来,抓起野藠秆,轻轻一甩,一颗颗泥土从根须上纷纷落下,快乐的心情也跟这泥沙般一样,纷纷扬扬,到处都是。不到一上午,我们就能挑满一篮子。
每次挑完野藠回家,母亲都会做一盘野藠炒鸡蛋,记忆里,那野藠的醇香和鸡蛋的爽滑,会让味蕾瞬间绽放,一种真实而温暖的幸福感直奔脑门而去。无怪乎,被誉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蔡澜会在《人间好玩》里这样描述:“能够把平常的食物变成佳肴,是艺术,不逊于绘画、文学和音乐。人生享受也。”
我想,对孩子而言,每一位母亲都是深懂艺术的人。
>>我要举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