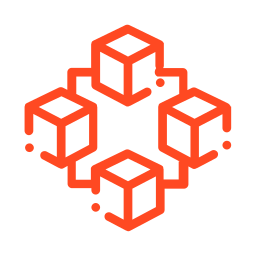抡斧劈柴
文 | 袁长江
大伯说,你们几兄弟,帮我去把那些柴劈了。
我说正月里拜年呢,劈什么柴,有人就说,柴好,正月里劈柴,一年都有财。我看见大伯哈哈大笑,看来这话是中他的下怀,说到他心窝窝里去了。大伯这几年见老,背越来越佝偻,像一弯犁铧,他家墙上仍然挂着木犁和竹笠,不过应该是多年没有使用,每年冬天他都会取下来,用桐油髤漆一下,说是春天潮湿腐烂或是秋天干燥开裂。我知道,他已经不能犁田,他的背和这木犁的弯曲度已经高度一致。
说是劈柴,其实是一株硕大的苦楝树,风吹雨打,树离房子越来越近,大伯担心会倒下来砸到房子,十几年的大树,一个小时不到就被砍倒截成一段段的木桩,树芯是那种好看的粉红色,可惜木柴并不致密,不然真的可以拿来车珠子把玩一下。苦楝树是杂树,生长速度快,但干后容易开裂,打不成家具也做不了正材,就连累累的果实也没什么用——中药里的川楝子就是这个玩意,但是本地的果实小而肉薄,并不能入药。十几年的大树,最终沦落成烧火的柴,实在也是可惜。这些年乡里的杂树大多难逃此运,先是枫树梓树,后来是喜树泡桐树,什么都一顿乱砍,然后种上修剪得齐齐整整的桂花树,栽在着意修葺的院落里,太精致的乡村让人心生喟叹,姑娘大嫂也都涂脂抹粉,失去原来的样子,不再有乡愁,不再有鲜明的春夏秋冬。
我们管劈柴的斧头叫“开山子”,从外观上还是有不少区别,开山子刀刃更窄背更厚,力道也更集中,一般是油茶树做的木柄,更结实耐用也更安全,古人文中“怀笛空吟闻笛赋,到乡还似烂柯人”,柯就是斧头的木柄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“烂柯”已经成为世事沧桑、如梦如幻、人物全非的代名词。或许哪一天,村庄里再也没有人烧柴也没有人用斧头,烂柯怕真的会成为现实。
别看我说得一套一套的,其实我啥也不会,啥也没干过,我至少有十年——大概或者我从来没有搬弄过斧头,我勒紧衣服,扎起马步,抡起开山子,那模样是不是很酷?想着是不是要来一句:“小刘海,在茅棚,别了娘亲……”刘海是花鼓戏《刘海砍樵》里的人物,樵夫是美称,其实就是砍柴的,说不定还没我帅,砍柴还能捡个老婆,实在是幸运之至。诗人海子说过:从明天起,做一个幸福的人,喂马,劈柴,周游世界。这么好,要不,我先劈柴如何?
忽然想起,去年深冬的时候我偶然去一个山冲里,正好遇见一位老人在劈柴,峰回路转间泥墙小瓦的老宅子,墙角整整齐齐地码着劈好的柴,乡村已经很少有这种老旧的院子,几乎和我印象中的村庄一模一样,什么都没改变。老人年事已高,身体却还硬朗,独自一人居住在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,其实他的子女都住在山外,我说你怎么不和他们同住,同行的熟人说他是舍不得婆婆子,我诧异地问婆婆子在哪里,老人没有言语,我才看到墙上的相片。那时节已经起了北风,我们走后不久就是风雪夜,我一直在想,那些劈柴,是不是能温暖老人的身,又或者,能不能温暖老人孤独的心。
开山子举了半天,式样摆足,照也已拍,废话说一大堆,就差没发个朋友圈,总不能只摆拍一下而无实际行动。嘿,劈柴!一斧子下去,苦楝树居然迎刃而开,这才想起,它木质松脆,不堪大用,只能做柴,可惜的是,才劈几下,我就觉得眼冒金星,天旋地转,双脚发软,一众弟兄都哈哈大笑。也难怪,我天天坐电脑前面,哪里多用过一分力气,咬着牙好不容易才坚持一会,幸而大伯大喊吃饭,我如遇大赦,斧头一扔,立马溜之大吉。
只觉得今天的菜格外香,愣是多吃了一碗饭。
>>我要举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