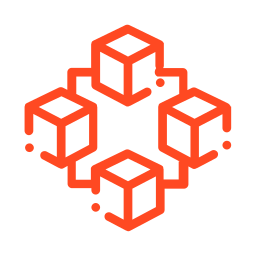不知洋芋谁怜惜
文 | 熊其雨
农历闰了一个月,田间草木不滋长。往年的三月,这种名为“三月黄”的果蔬,早就应该“躺平”在餐桌和空气炸锅里了。农家喊它为洋芋头,城里人唤做土豆、马铃薯,其貌不扬圆滚滚,大抵是“舶来品”的缘故,帮它灰头土脸的外表平添了几分洋气。
对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湘北农人而言,平凡的岁月,由酸菜、蓑衣萝卜和洋芋头交织,清苦却丰盈。初春,矮胖的陶米缸和敞口瓜瓢里,软皱的洋芋头上冒出青紫色芽苗。捞起切块,在冷却的草木灰里打个滚,消毒后就可以种植了。在田间开好浅沟、挖好蔸坑,下种时使芽眼朝上,既利于土豆发芽,又可促进土豆块茎形成并长大。清明前后,嫩绿豆苗下的土堆,踩着早春的脚步“发福”,从缝隙中冒出一串串皮白色黄的小芋头,用手抠出其中的大果再盖好土。此时,洋芋初长成,鲜嫩且难得。
它们不知有几多无忧无虑,出落于泥土之间,披着或白或紫红的薄绸,用手一擦可轻松去掉表皮,胖瘦者皆可赏味,不怒也不争。突然想起有一年走亲访友,在猪栏屋发现一根造型别致的木质器具,仔细问询年长者方知,早年农村用陶罐煨煮汤水或中药时,由于灶里有余温,罐体表面温度较高,为防止烫到手,每家每户都制作了长一米多,一端有两根粗木齿的“助手”,名为拖罐把。闲暇时分,拖罐把也不会被大材小用,它的“副业”是剥洋芋头皮。把洋芋头倒在水桶,井水没过后,拿拖罐把沿着桶身上下左右反复捯饬,洋芋头表皮自然脱落,内里却光滑无损。
有位在长沙生活三十多年的乡友,总感叹吃不到霉豆渣、白皮土黄瓜和潘家辣椒等儿时味,我深有同感,却笑他大肚便便,每天被鸡鸭鱼肉“围攻”。仔细想来,他的话也并非道理全无,仅以洋芋头来打比方,那种不施肥不打药,孩提之时吃到发腻,个头小、黄心、好撕皮的品种,在菜市场无可寻觅。买到的呢,一律是一斤多重的白心土豆,炸薯条也好,炒土豆丝也罢,吃的无非是些调料味,食材本身却细嚼无味。
忙碌的日子里,风华不过一日三餐,总念去田园和归去。每每有人感叹人生,常让我泪眼婆娑。多年前,奶奶家楼梯的拐角处,总堆放着一地糊着泥巴的洋芋头,有无意中挖破的,也有大小不一、形状各异的。每次回家,我都要带一些回来,开汤、红烧,或蒸熟撕皮捣碎后做土豆泥,放麻油和生抽拌匀,是早餐的佳品。当然,其经典吃法无非是大道至简,清澈自然。猪油烧热,土豆切片,炒制后开汤放淡盐和一小片桂皮,起锅时撒紫苏和葱花,洋芋头软糯甘甜,可以扒得几碗饭。
正是闰月里,无暇归去也。洋芋头熟了,无肉也可欢。
>>我要举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