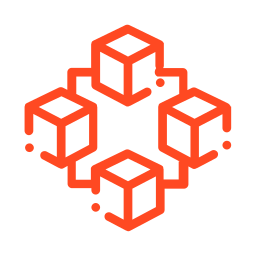黄骨咯咯
文 | 彭梦宁
近读汪曾祺《故乡的食物》,里面有这样一段文字:“昂嗤鱼阔嘴有须,背黄腹白,无背鳍,背上有一根硬骨,捏住硬骨,它会‘昂嗤昂嗤’地叫。”以叫声给动物命名,并不鲜见,比如知了、布谷鸟等等。最有意思的是蛤蚧,蛤蚧因声而名,雄者叫声为蛤,雌者叫声为蚧,遂以鸣声命名并流传至今。
毫无疑问,汪曾祺笔下的昂嗤鱼,其实就是黄骨鱼,只是这个拟声词有待商榷。在我的家乡,此鱼多是“咯咯”地叫,我们又把黄骨叫做咯骨。造成这一差异,除了地缘关系外,还有方言因素。闻香识女人,听声辨亲人,语言差异再大,只要不妨碍交流就行。假设我们家乡的咯骨,尾巴摇几摇,游到汪曾祺的故乡苏北,那里的昂嗤定会热情相拥。不过欢迎之余,肯定有昂嗤老大发问:“兄弟,听口音,你好像是外地来的吧?”
中国地大物博,同物异名就是地域文化的鲜明特色。黄骨学名黄颡,属于鲶形目,鲿科,黄颡鱼属。不同的地方,有不同的叫法,如东北叫嘎牙子、四川叫黄辣丁、湖南叫黄鸭叫等等,如此种种,不一而足。如果谁要纠结写法的对错,那本身就是犯了最大的错。据实物考证,早在两千多年前,川蜀一带就开始日常食用黄颡了。而最早记载黄颡的,是《小雅·鱼丽》:“鱼丽于罶,鲿鲨。君子有酒,旨且多。”这里的鲿,指的就是黄颡。
如此说来,黄骨很早就成为了下酒菜。在儿时记忆里,黄骨并不受待见,这家伙个体瘦小,好像永远长不大,在一般的沟渠河湖里,顶多只有三四寸长。最烦心的,是这家伙长有三根可以闭合与立起的毒刺,如果在水里不小心摸到它,就会立刻遭到三箭齐发的攻击,“唉哟”一声的惨叫随之传来。即便是在岸坡上,想抓住黄骨,也得小心翼翼,必须五指张开,使之利刺夹于指间。
若干年前,我曾与一朋友去野湖垂钓,走了近一个小时的泥巴路才到达钓点。没钓一会儿,突然下起了大雨,正准备责怪一下老天,忽然浮漂猛地一沉,我下意识地把鱼竿一提,居然拉起一条筷子长的黄骨。取钩的时候,它不停地抖动着利刺,发出“咯咯”的声音,简直就像唱歌一样。更不可思议的是,那天在狂风暴雨中,钓了十几条大黄骨,乐得我忍不住手舞足蹈。正所谓乐极生悲,晚上回家料理它们的时候,手指居然被刺到了,鲜血没流多少,可钻心的疼痛让我无法入睡。
野生黄骨味道鲜美,营养丰富,与人工养殖的有云泥之别。每次钓到黄骨,我都用心侍弄,生怕糟蹋了这不可多得的食材。鱼贩杀黄骨,过于简单粗暴,都是抠其鳃,顺势向下拉,直至将鱼腹撕开。这样杀出来的鱼,品相自然不好,吃起来总感觉有些膈应。不像鲫鱼,黄骨只一根主刺,老人小孩都喜欢吃。黄骨的常见做法有很多,可煲汤,可红烧,可清蒸,随便选哪一样,都不会有吃亏上当的感觉。
或许是年龄渐大的缘故,我现在越来越不喜欢吃肉,不管是羊肉牛肉,一不小心就塞牙了,不得不弄根牙签鼓捣半天。还是吃鱼好,尤其是野生黄骨,筷子一挑,半边鱼肉滑落,既可囫囵吞枣,也可细嚼慢咽,除了享受还是享受。吃黄骨,我最爱的还是火锅,汤汁浓郁,越煮越入味,一口黄骨,一口白酒,惬意无比。尤其是吃完鱼身鱼尾,再夹起鱼头,吮吸鱼脸颊肉,感觉是如此嫩滑,简直是飞一般的感觉。
鱼脸颊肉,又叫月牙肉,乃鱼腮帮子上一小块似月牙状的肉。会吃鱼的人,绝对不会在意刺多还是刺少,而是越稀缺的部位越有诱惑力。作家沈从文曾写过一个故事,说以前的土匪绑架孩子,会先饿上两天,然后给他做一条鱼吃。如果一上来就挑鱼背上的肉,说明是穷人家的孩子,立马就放了;如果一上来吃的是鱼肚皮,会先扣几天,看能不能讲价还价;如果一上来专找鱼脸颊肉吃,那对不起,终于干一票大的了。
当土匪化身美食家,遭殃的就不只是鱼了,还有那些只知道娇生惯养的家长。或许正是深谙此理,为了防止成为帮凶,黄骨才会长出毒刺,并发出“咯咯”的声音,以此表达抗议。我决定,从此以后,我也要学大富人家,先从脸颊肉吃起。有些优雅,学不会,难道还装不会?
>>我要举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