亚坤夜读丨蔡皋:底色(有声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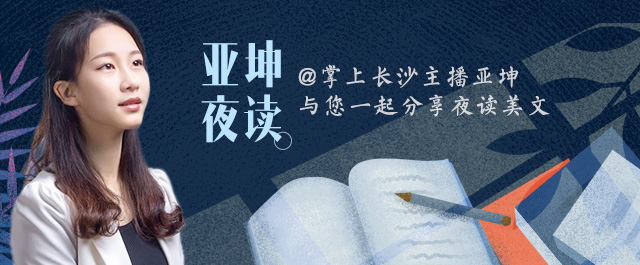
在做《记得当时年纪小》这套书时,我问自己,我为什么要做它,我还问自己,我的作品是什么?
我的作品是什么?它像是一泓清水,不大不小,刚好照见我的天光和云影,照见我的生活。
我的生活和我的作品多与儿童、与民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它们有时以图画书的形式,有时以单幅画或其他形式出现,我都会看到它们在精神上的那种叠合。在童书里讲不够的东西,挪到面向成人的作品中去讲,成人作品里展示不了的东西,复又归到图画书里去做。如此看来,我的作品好似南方女子做的那种叫“双面绣”的针线活。
我喜欢针线活,喜欢绣女们制作绣品时单纯而专注的心思。在我看来,画家创作时的态度与绣女们一样,心中应有特定的对象,并怀有温暖的心思,那种作品是能打动人的。
我开始画画,且有种大胆的作风,则要归功于我全家的宽容。我爸一年四季在外头做事,自然对我们是大宽容。外婆和我翁妈,加上放假归家的姨妈——一位表演天才,都是戏迷。她们不仅让我看戏,参与她们外交,而且送我颜色,加起来就是大宽松。在没有颜色之前,我会从床脚下耐烦地摸找松软的木炭,在一张张门背后的粉墙上画大型壁画,乱七八糟,墨墨黑黑,她们也不骂我。我的芳邻齐嫂子,则或背或抱着她的小宝宝站在我背后紧看,意犹未尽之时居然请我去她家的门背后也画它一幅,让我这个“画家”着实兴奋了一把。我有几个读者?包括那个小宝宝,我妹子,有一桌人咧!
童年的天空,飘着风筝;童年的衣服,花花绿绿;童年的气息,混合栀子花和茉莉花的异香;童年的色彩,传说一样奇妙。我找童年,同时找到了民间。原来,我本民间,朴素深厚的、充满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民间。
在我懂得去一所好的学校可以继续读到好书的年月,我被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录取。湖南一师学校是个师资力量强、藏书很丰富的学校,我欢喜不尽地在那儿读了一些好书。我的美术课王正德老师、语文课曾令衡老师皆是很会上课、很有本事的人,这样的老师第一师范还有不少。我听他们的课总有神采飞扬之感。我欢喜我的母校,虽然所有的欢喜皆有不欢喜卧底,但我把它们加起来喜欢,我喜欢我敬爱的老师和可爱的同学们。在那段慷慨激昂的岁月,我们班级称得上波澜不惊,我在这种对比关系中完成人生初步的预备功课,这种功课使我在走向社会时已懂得了什么是我根本的需要。
毕业之后,在株洲县文化馆敬绘了一年的毛主席像,然后去了该县最为偏僻的山区太湖小学当一名教师。太湖并没有湖,“太”字是方言“大”的谐音。之所以叫作太湖,是因为当地山与山之间的谷地如绿浪滚滚,其状若湖。
我喜欢山村,我所在的学校由古祠改建,祠里的六朝松依然顶一团绿荫,上下课的钟声敲响,远近山谷都有回声,这可爱的田亩、山谷因钟声而平添了一种禅意。
山村的一草一木,一山一水,在我全是一个好。上课堂堂进,下课当农民,无论如何辛苦,这个已知春插秋收、砍柴担水“无非妙道”的人已存有一种念想——在生活的艰苦中体味人生深层的喜乐的念想。我的思想境界渐趋明朗,我的生活也日日是好日地好起来。

走笔至此,底色已显。我的朋友,你们已大致看到我的从前。往下看,我作品中的东西兴许会来帮我再作些许补充,它们毕竟是底色之上的意象和笔触,有它们自己说话的方式。
我常问自己:你爱“好”,“好”是什么咧?是针好、线好、材料好?“好”,是一种心思。心思一好,一切皆好。即使手法生一点,兴许还会有助于一种蠢蠢的“好”的表达。“好”是一种能力,使一切手法的表达能力变得有了自由度。

>>我要举报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