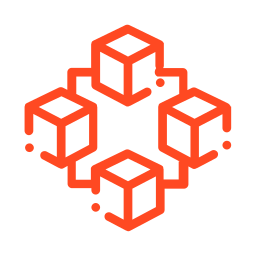那簇老树
刘际雄
还是凌晨,屋外的鸟儿耐不住寂静,将欢快的叫声送进耳鼓。循声望向窗外那一排宿着鸟的树,脑中蓦地闪出一簇虬干参天的古树来。
那是故乡的老樟树!六十年前,在老家,这样的老樟树随处可见。或伺立于庙观,或环依于农舍,老樟树雄奇挺拔,透着历史的厚重与沧桑。
脑中闪现的那一簇老树,兀立在生我养我的老屋旁。听长者说,树为刘家老祖宗永圣婆婆手植,距今凡八百来年矣。树群有七八棵,大的四五人合抱不来,小的也要两三人牵手去量。树将枝干横伸旁逸,交织成一片遮天蔽日的冠盖。树之根则隐隐突突,如虬龙般交缠在一起。
树大招鸟,密密匝匝的冠盖里,住着各种各样的鸟。喜鹊、画眉、斑鸠、黄鹂……每到清晨,鸟便此起彼伏,将欢快的啼鸣织成动人的交响。农人们亦闻鸟起舞,开始一天的营生。
在树中捉迷藏是儿时恒常的向往。每逢晴日,或晨或昏,一帮孩子在树林里聚了,捉捉藏藏,嬉戏笑闹,把树上的鸟儿惊得扑棱棱飞。老树好几棵身上都开着幽幽的洞,那些树洞便是我常选的藏处。一俟负责找人的儿伴将眼睛蒙了,便寻个窄小的树洞钻将进去,把身子矮了,再悠悠地喊上一声:嘟嘟!儿伴便睁开眼来,循声寻去。寻着了,彼此一声惊叫,然后便是一串开怀无忌的欢笑。倘久寻未得,儿伴失了兴趣,怏怏走开,我便从那洞中探出头来,甜叫:我在这儿呢!
若是暑天,那片林子便是绝好的避暑胜地。一到夜来,吃罢晚饭的爷们和一帮孩子,便光着膀子,背把躺椅,或拎张草席,搬把椅子,到树下集体纳凉。风从高挂在树上的叶儿中习习而下,拂在脸上,掠过胸前,拭遍周身,感受似六月天喝凉水般的爽!禁不住这难得的惬意,老少爷们常常会拉开长腔,带了咏叹,朗朗地亮出一嗓特有的曲调:风儿凉啊,嗬——喂!
砍树的决定不知是谁做出的,也不知当时为啥要取了那簇老树的性命!询及年逾八旬的父亲,他也说不清楚。只记得,当年生产队用新法育秧,在田底下挖了洞,须日夜烧火加温。许是柴禾不够,才打上了老树的主意。
砍树那天,一村老少都齐围在林子周边,看老树上路。有个头小身子短的,站在圈外,像一群被无形的手提了脖子的鸭,拼命地向里张望。斧头是砍不断的,得用拉锯。执锯的是两个膀粗腰圆的汉子,各自拿了锯柄,弓下腰,向着老树拼命地来回拉。“咯哧咯哧”,锯齿出处,带出的木屑白中透红,像是老树殷殷的血!不知过了多久,大汉早已赤裸了上身,头顶热气腾腾,身上汗水涔涔。“倒了,倒了!”听得一声喊,看着的人猛地四散,那棵最大的老树竟轰然倒地,砸起尘土一片!树上密密匝匝的叶委顿一地,兀自不停颤动着身子,发出“咿咿哟哟”的响声。我想,那定是老树的痉挛和哀鸣吧,不知含了多深的悲和怨!
那老树林,就这样在儿时的生活里消失了!消失得无踪无影。但老树高大的身躯,树顶密密的冠盖,脚下盘错如虬龙的根,连同鸟儿欢快的啼叫,儿伴游戏的喧闹,和那纳凉时惬意的歌调,都深深刻在我心,60年挥之不去,历久弥新。
这些年也常回老家。四野的山是葱茏得多了,连路也没于无边的荆棘。可怎么也见不着儿时那样的老树了。偶有一株大点的树,近前观看,虽不足合抱,倒也挺拔,独秀于一片林中。那许是老树的孙子辈吧,要长成树爷爷的模样,还得多少年啊!何况,它只是孤孤的一棵呢!
>>我要举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