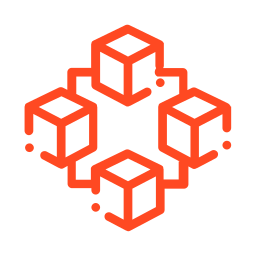我怎能不歌唱
康俊宇
八十年前的土地上,硝烟与呐喊曾谱成一曲悲壮的交响。鼓书艺人方宝庆望着苦难中的孩子哽咽失语,艾青笔下的鸟儿用嘶哑的喉咙啼血歌唱,穆旦以带血的手拥抱站立的民族,我听见历史的血脉里奔涌着同一个声音:对土地的热爱,对新生的渴望,对血脉中不屈精神的传承——这,就是我们民族的灵魂之歌,让每一个子孙都不得不以生命和热忱应和。
哽咽中的沉默,埋下歌声的伏笔。曾几何时,国家蒙辱、人民蒙难、文明蒙尘,老舍笔下的方宝庆“开不了口”,恰恰是旧时代艺人的觉醒。在《鼓书艺人》的烟尘里,他目睹山河破碎,看见孩子们在战火中流离失所。那一声哽咽里,藏着传统艺人的赤子之心。这种沉默不是麻木,而是爱到深处的震颤。方宝庆最终会开口的,正如沦陷区的百姓终将拿起锄头与扁担——当热爱沉淀为责任,沉默便成为歌唱的序章。
嘶哑的喉咙,唱破黎明前的黑暗。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?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。”艾青的诗行如刺刀,划破战争的浓雾。那只“用嘶哑的喉咙歌唱”的鸟,正是千万个以笔为枪的知识分子的缩影:田间在《假使我们不去打仗》里怒吼,萧红在《生死场》中泣血,他们的呐喊,让文明的火种在焦土上燃烧。这种歌唱无关技巧,只关信仰,就像西北高原上的信天游,吼破黄沙的是牧羊人对土地的执念。北平学生喊出“停止内战,一致抗日”,西南联大师生在敌机轰炸中坚持弦歌不辍,他们都是艾青诗中的鸟,有带血的喉咙,有一颗与土地同频共振的心。
带血的手,拥抱新生的民族。那些在淞沪战场上用肉身筑城的士兵,那些在滇缅公路上客死异乡的华侨机工,那些在“大生产运动”中挥汗如雨的延安军民,他们的手掌都刻着民族觉醒的密码。这双手曾在南京大屠杀的废墟上捡拾白骨,又在不到三十年后托起第一颗原子弹;曾在北大荒的雪地里扶犁开荒,又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织就锦绣山河。我们看见工人农民布满老茧的手指,看见脱贫攻坚一线的年轻干部磨破的手套,看见抗疫医护被汗水泡皱的手掌。我们看见,穆旦笔下的“拥抱”从未停止,那是历经苦难的民族对新生的热烈回应,是千万双手共同编织的复兴图景。
站在历史的长河边回望,前辈们的哽咽、嘶哑和血迹,早已在岁月中酿成一曲雄浑的合唱。如今的我们,或许不必再用喉咙嘶吼,但那些沉淀在民族血脉里的热爱与坚韧,依然需要我们用行动去歌唱。因为每一个灵魂都会听见内心的召唤:这土地曾如此伤痕累累,又如此生生不息,我怎能不歌唱?
当代中国,江山壮丽、人民豪迈、前程远大,让我们以责任为弦、热忱为调、坚韧为谱,在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的征程中,唱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最强音——因为“一个民族已经起来”,因为我们“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”!
>>我要举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