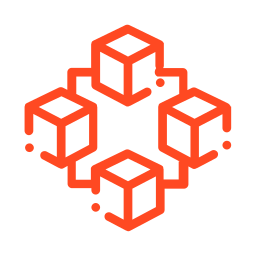这声音或许不完美
罗仲良
老舍笔下鼓书艺人开不了口的焦灼,艾青嘶哑喉咙里的歌唱,穆旦带血双手的拥抱,勾勒出人类永恒的精神图谱——在失语与呐喊的撕扯间,寻找生命的重量与意义。而这些文学作品中的灵魂挣扎,最终都在平凡人的故事里化作震撼人心的现实映照。
城郊那片菜园总飘着泥土香,自从父亲走后,母亲就成了这里的守望者。褪色的蓝布围裙系在她脊背弯成岁月的弓的腰间,粗糙的手掌握着锄头,一下又一下翻松土地。她把对父亲的思念、对远方孩子的牵挂,都埋进这方土地里。春天,她佝偻着背种下一排排辣椒苗;夏天,踮脚摘下最鲜嫩的黄瓜;秋天,轻轻擦拭金黄的南瓜;冬天,裹着旧棉袄埋下希望的种子。每个周末,她都早早站在路口张望,风吹乱花白的头发也浑然不觉。
那年强风过境,暴雨如注。半夜两点,我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,是邻居打来的:“快来看看你妈,她在菜园里……”我心急如焚地赶到,远远看见母亲举着破旧的塑料布,在风雨中拼命护住那片番茄苗。雨水顺着她的脸颊滑落,混着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。“这是你爸和孙娃的念想!”她冲着我喊,声音被风雨撕扯得破碎。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,这片沉默的菜园里,藏着她震耳欲聋的爱。
沉默的力量不仅藏在土地里,也绽放在无声的语言中。在群山环抱的村落间,总能看见栗老师骑着锈迹斑斑的二八自行车穿梭的身影,铃铛声像一首沙哑的老歌。这位退休语文教师,偶然接触到村里的两个聋哑儿童阿明和小夏,便决心自学哑语。泛黄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手语动作,电视里的手语新闻成了她最忠实的老师。
每个周末的清晨,她的小院都会准时“热闹”起来。阳光透过糊着报纸的窗户,在小黑板上投下菱形光斑,栗老师的影子与手语动作交织成一幅动态的画。她用布满老年斑的手,比画出孙悟空腾云驾雾的模样,讲述《西游记》的故事时,眉毛也跟着上下飞舞。当她比画到三打白骨精被误解,阿明和小夏着急地用手语“追问”,她笑着轻轻点头,继续讲述师徒重归于好的情节。
阿明是个内向的少年,因听障曾十分自卑。栗老师发现他喜欢画画后,便在讲《千里江山图》时,特意带他临摹古画。“江河浩渺,群山巍峨。”栗老师的手语与阿明的画笔默契配合。渐渐地,阿明开始主动用手语分享自己的画作,还创作了一首手语诗歌送给栗老师。年末,栗老师组织了“手语村晚”节目,手把手教大家用手语“唱”《春节序曲》,院子里飞舞的手语,比任何声音都要热闹。
村子一角的废品站里,堆积如山的纸箱后藏着一架旧钢琴。收废品的老张总在傍晚偷偷掀开琴盖,用缠着创可贴的手指,磕磕绊绊地弹《致爱丽丝》。那年女儿想学琴,他咬咬牙买了这架二手钢琴,却在送货路上遭遇车祸,一块废铁砸碎了他的喉骨。如今女儿在大城市成家,他守着这架钢琴,把对女儿的愧疚谱成不成调的曲子。
直到那个深秋,女儿带着外孙突然返乡。当老张僵硬的手指再次触碰琴键,外孙好奇地趴在琴凳上模仿,女儿眼眶泛起潮汐,轻声说:“爸,您弹得真好听。”三代人围在斑驳的钢琴旁,听着不完美的琴声欢笑。这一刻,沉默多年的愧疚与思念,都化作了流淌的音符。
从母亲菜园里沉默生长的倔强,到栗老师指尖流淌的文化火种,老张琴键上跳动的愧疚与温柔,我们看见:失语从不是终点,而是孕育力量的温床。在信息爆炸却充斥表达焦虑的时代,有人因困顿或麻木选择沉默,有人因现实压力被迫失语。但正如穆旦“以带血的手拥抱”,当个体的沉默化作改变的勇气,当困境中的坚持凝聚成群体的共鸣,失语终将破茧为蝶,化作时代的最强音。
这声音或许不完美,却足够真实;或许不宏大,却足够震撼——因为每一次冲破失语的尝试,都是对生命最庄严的礼赞。
>>我要举报